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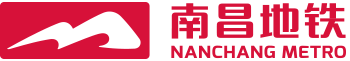
南昌地铁运营十周年征文大赛优秀作品展播
发布时间:
2025-11-15 00:00
来源:
党群工作部综合整理
访问量:
十年,一段流动的时光,一趟温暖的旅程。 在南昌地铁运营十周年之际,我们发起的“拾光 与美好同行”征文大赛,如同投入时光长河的一颗石子,激起了无数动人的涟漪。 感谢您,用文字回应我们的十年。 自活动开启,我们便在海量的投稿中,一次次被深深打动。那些真挚的笔触、沉静的回望……每一篇,都是一扇窗口,让我们得以窥见这南昌地铁与这座城市十年来的脉动与温情,感受地铁如何悄然改变着每个人的生活,汇聚成磅礴而温暖的力量。
现在,是时候将这些闪耀着光芒的优秀作品,正式呈现在您面前。这里,有南昌地铁十年奋斗的坚实足迹,更有您与这座城市同行的独家记忆。
一碗粉,一条江,一趟车
贾 莹
我是个兰州人。
这话一说出口,嘴里彷佛就泛起一股子牛骨汤的醇厚味道。我们兰州,是被夹在两山一河之间的一条儿,像一根抻得长长的面。城市是这么个直来直去的脾性,人也是。风是硬的,吹在脸上像用砂纸打磨。太阳是毒的,能把柏油路晒化。但只要一碗头锅的牛肉面下肚,那点子燥气就全被熨帖下去了。我们的河,是黄河,水是黄的,里面卷着沙,奔腾起来,是千军万马的气势。我们看惯了黄土高坡的苍凉,习惯了空气里那股子干燥的、带着尘土味的踏实。
所以,头一回到南昌,我是真有些犯怵。
那是为了儿子。他考上了这里的大学,我和老伴不放心,就收拾了家当,跟了过来。火车一到站,车门开处,一股子又湿又热的气浪,兜头就将我整个儿给“焖”住了。那感觉,没法说。不像是蒸笼,蒸笼好歹还有个盖子。这就像是整个人被泡进了一锅温吞的热水里,水里还长满了黏糊糊的水草,缠着你,裹着你,让你每个毛孔都透不过气来。老伴扯着我的衣角,只说了一句:“天呐,这地方的水,怕是不要钱的。”
可不是不要钱么。赣江,抚河,艾溪湖,象湖……水网密布,把整个城市浸泡得汪汪的。连空气都是湿的,墙角能渗出水,席子睡几天就发黏。这对于一个在西北待了一辈子的“干人”来说,浑身都是别扭。
那几年,南昌正在为一件大事“翻肚子”——修地铁。满城都是蓝色的铁皮围挡,像给城市贴满了巨大的创可贴。路被挤占得只剩一条缝,公交车在里面“吭哧吭哧”地爬,像得了哮喘病的老牛。我们住在城东,儿子学校在城西,去看他一趟,是桩大工程。得先坐一趟车,到八一广场,再换一趟。车上人挤人,汗流浃背,混着各种气味。我总觉得,南昌人的夏天,一半的汗,是流在公交车上的。
那时候,我们对这座城市的印象,就是“堵”和“吵”。围挡后面,日夜不休地传来“哐当、哐当”的声响,沉闷,执着,像是有一头巨大的钢铁穿山甲,在地底下不知疲倦地啃着石头。儿子总在电话里说:“爸,妈,再忍忍,等地铁通了,就好了,我接你们就方便了。”
地铁。这俩字,听着就洋气,离我们的生活,彷佛隔着一层。
终于,1号线通了。红色的,像一条喜庆的飘带。
儿子特意选了个周末,带我们老两口去“开洋荤”。从艾溪湖东站的口下去,世界瞬间就变了。地面上那股子要把人煮熟的暑气,被一道无形的门给隔绝了。一股子清凉、干爽的风,带着点新机器特有的、好闻的铁腥味儿,迎面扑来。我贪婪地深吸了好几口,感觉五脏六腑都被这阵风给洗了一遍。我对老伴说:“嘿,这敢情好,跟咱们兰州挖的地窖一个功效!”
站台光洁如镜,能照出我花白的头发。一切都是新的,齐整的。大家安安静静地排队,车来了,“嘀嘀嘀”几声,门就悄无声息地滑开了。我们上了车,找了个位子坐下。车厢里冷气开得足,坐久了甚至有点凉。列车开动,极其平稳,几乎感觉不到一丝晃动,只听见一种持续而轻微的“嗡嗡”声,像是远处传来的一首安眠曲。
我看着窗外,隧道里黑黢黢的,只有灯带飞速地后退,偶尔闪过一个紧急出口的标志。人坐在里面,有一种不真实感,彷佛是坐在一个时间的胶囊里,被一种强大而温柔的力量,推着往前飞。
那一瞬间,我心里头猛地一震。在兰州,我们也坐地铁,也从黄河底下穿过去。但黄河给人的感觉是雄浑、苍劲,甚至是悲壮的,像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。而这赣江,是温润的,开阔的,它所孕育的城市,有一种蓬勃的、崭新的、水灵灵的俊秀。就在那一刻,我忽然觉得,我跟这座一直让我感到“水土不服”的城市,有了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亲近。
从那天起,地铁,就成了我和老伴的“腿”,或者说,是我们的“船”。
我们开始研究那张线路图,红的、绿的、蓝的线,像城市的血管。它把这座对我们来说一度巨大而陌生的城市,变得清晰而有条理了。它不仅仅是一张交通图,更是我们探索南昌的“藏宝图”。
我们兰州人,对吃的执念,是刻在骨子里的。一碗面的好坏,关乎一天的心情。在南昌,我们起初是吃不惯的。什么东西都放辣椒,而且是那种湿漉漉的、鲜亮的辣,不像我们西北的油泼辣子,是干香。后来,儿子说,地道的南昌味道,不在大马路上,全在小街小巷里。于是,地铁就成了我们的“美食渡船”。
我们坐4号线,去绳金塔。出了地铁口,空气里就飘着一股子浓郁的油香、酱香,还有若有若无的中药香。我们摸索着,找到一家小店,门口支着一个巨大的瓦罐,黑得油亮。我们要一罐墨鱼肉饼汤,一罐鸡脚汤。那汤,清亮见底,味道却极醇厚,是慢火“煨”出来的功夫。再来两份拌粉,粉是圆的,粗的,极有韧性。店家手脚麻利地浇上酱油、辣椒、咸菜末、花生米、葱花,我们自己再加一勺店家秘制的萝卜干。稀里哗啦一拌,那香气,直往鼻子里钻。我吃得满头大汗,嘴里“嘶嘶”哈哈的,心里却畅快得很。我会想起我们兰州的酿皮子,也是要放很多调料,但酿皮子是凉的,口感是软糯的。这拌粉,是温的,口感是爽滑的。南昌人把对生活的热闹和精细,全拌在了这一碗粉里。
我们也会坐1号线,去万寿宫。那里是老城,地铁口一出来,就彷佛是穿越了。街是窄的,房子是旧的,但人声鼎沸,充满了烟火气。我们专为一碗“糊羹”而去。拿个小碗盛着,稠乎乎的,里面有鸡胗丁、豆干丁、香菇丁、笋丁……撒上雪白的胡椒粉,用小勺子一勺一勺地舀着吃,又烫又鲜,吃完,额头上会冒出一层细汗,从里到外都暖和了。老伴说,这东西,跟咱们兰州的“甜醅”有点像,都是那种不当饭、但吃了心里就舒坦的零嘴儿。
靠着地铁,我们像两个好奇的孩子,把南昌的味道,一点点地装进了肚里,也装进了心里。地铁的车轮“嗡嗡”地转,载着我们去品尝一碗粉,一盒糕,一块糖。每一次出发,都满怀期待。这趟地下的铁船,把城市的五脏六腑都串联了起来,然后慷慨地向我们这些异乡人,一一打开。
在地铁里待久了,人也看得多了。
南昌人说话,调子是往上扬的,像在唱歌,我们听不懂,但觉得热闹。早晚高峰,人潮汹涌,但自有一种秩序。年轻人给老人让座,是顶自然不过的事,有时候甚至不用说话,一个眼神,一个手势,就完成了。我见过一个穿着体面的中年男人,手里提着一袋子刚从菜场买的藜蒿,那是南昌春天特有的菜,有股子异香。他就那么自然地提着,神色安然。那一刻,我觉得,这才是生活本来的样子,再光鲜的写字楼精英,也要回家炒一盘藜蒿炒腊肉。
有一次冬天,南昌的冬天是湿冷的,冷到骨头缝里。车上,一个年轻的父亲,把三四岁的女儿抱在怀里,把孩子两只冻得通红的小手,塞进自己宽大的棉衣里,贴着自己胸口的皮肤取暖。孩子在他怀里,仰起脸,满足地叹了口气,像一只找到了暖炉的小猫。那位父亲没说什么,只是低头,用下巴轻轻蹭了蹭女儿的额头。整个车厢里的人来来往往,吵吵嚷嚷,但他们父女俩周围,彷佛有一层温暖而安静的光。我看着,心里那点子被湿冷天气勾起来的烦躁,不知不觉就散了。
这地下的铁龙,走得快,日子,溜得也快。
一晃,近十年就过去了。儿子毕了业,在南昌找了工作,娶了媳妇,安了家。我们老两口,也就名正言顺地从“陪读”变成了“常住”。孙子出生那天,我跟老伴从城东的家里,坐地铁去省妇幼。一路上,车厢轻轻地摇,我的心也跟着,一下一下地,激动得没个着落。老伴嘴里念叨着:“可不敢耽搁,可不敢耽搁。”我嘴上说她瞎操心,其实自己手心里也全是汗。那一次,觉得地铁跑得真快,可心里又盼着它能再快一点。
孙子渐渐长大了,会说话了,会跑了。地铁,又成了我们祖孙三代的“游乐场”。周末,儿子媳妇忙,我们就担起了带孙子的重任。“爷爷,我们今天去坐‘地洞里的小火车’!”孙子口齿不清地喊着。于是,我们就一人牵着他一只小手,坐上地铁,去八一公园看大象,去瑶湖森林公园放风筝,去秋水广场等晚上的音乐喷泉。
我印象最深的一次,是带他去看喷泉。我们坐2号线,到了学府大道东站。孙子一路兴奋,在车厢里指着窗外的灯光,大呼小叫。到了站,他挣开我的手,自己“噔噔噔”地往扶梯上跑。我跟在后头,看着他小小的背影,忽然一阵恍惚。我想起了十年前,也是在这条线上,儿子也是这样年轻,带着初来乍到的我们,去看江对岸的风景。如今,风景还在,只是身边的人,多了一个更小的。
地铁的线路,也从当年那孤零零的一条红线,变成了如今纵横交错的一张大网。2号线、3号线、4号线……它们像这座城市新生的血管,把南昌的东南西北,都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。我们家的墙上,贴着一张最新的地铁线路图。有时候,我会戴上老花镜,用手指头在上头比比划划,从我们家,到儿子家,到孙子将来可能要上的幼儿园,再到我们常去的菜市场、医院……都清清楚楚,都能“坐着小火车”去。这张图,就是我们在南昌的“根系图”。
我还是会时常想念兰州。想念那碗汤清、萝卜白、辣子红的牛肉面。想念黄河边上,被风吹得有些粗砺的空气。那是一种深入骨髓的、故乡的味道。但说实话,若现在真要我搬回去,我怕是会舍不得了。
我会舍不得清晨去菜场买的那一把水灵灵的小菜,舍不得傍晚在艾溪湖湿地公园散步时,拂过脸颊的、带着水汽的风,舍不得街坊邻居那听不大懂、却觉得很亲切的南昌话。我更舍不得的,是这趟已经坐了快十年的“地洞里的小火车”。
它早已不是一个冷冰冰的交通工具了。它是我和老伴的腿,是孙子的摇篮,是我们一家人情感的连接线。它的一头,载着我们初来乍到时的陌生与不安;另一头,载着我们如今安稳踏实的、含饴弄孙的晚年。它在黑暗的地下穿行,把我们从一个地方,运送到另一个地方;也在时光的隧道里穿行,把我们从人生的一个阶段,运送到了另一个阶段。
“拾光·与美好同行”,这话说得真好。这十年,我们就是坐在这趟地铁上,一点一点地,把在南昌的陌生日子,过成了熟悉的、有滋有味的生活。我们捡拾起的,是孙子的笑声,是老伴的唠叨,是儿子媳妇的关爱,是这座城市不经意间流露出的温情。这些点点滴滴的美好,都随着地铁的节奏,融入了我们的生命。
如今,我偶尔还会一个人,什么事也不为,就去坐地铁。从起点,到终点,再从终点,坐回来。我看着车厢里那些年轻的、疲惫的、充满希望的脸,就像看着一条河流。河流里,有我,有我的家人,也有这座城市里千千万万的普通人。列车向前,日子也向前。
轰隆轰隆,下一站,不知道又会是什么样的风景。
但心里头,是踏实的。这样,就很好。
分享到: